|
海外代充值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早年婚姻没有结果,结婚没几年就离婚了,孩子是跟着我的,离婚之后我被优质男求婚,原以为是幸福的开始,但没想到我不仅沦为他的发泄工作,因为我床上功夫好才看上我,而且他竟然还卷走了我的钱。 我第一次见到我外婆,是在监牢的探监室里。 那时我还小,母亲拉着我的小手,带我走进一个昏暗的小房子里。我依稀记得那天,一团团乌云侵蚀了铅灰色的天空。抬头望去,滴滴小雨坠落在我稚嫩的面庞上,阴凉的风拂过我额前刘海。 我很害怕雷雨天,内心深处隐隐害怕起来。站在一旁的母亲用她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攥住我,往她怀里拥。 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房间,我看见一排排的小窗口,透明的玻璃墙和长台无情地将空间划成两边,我望见窗口的那边,穿着蓝白条纹衫的老妇人步履蹒跚地朝我们走来,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 老妇人面色苍白,宽大条纹衫在她身上如同漂浮着的衣料,她微低着头,步伐缓慢迟钝,可在看到母亲后,眼珠子熠熠亮起光芒来。 我站在母亲身旁,眼睛圆碌碌地打量着与我隔着一层玻璃的老妇人,我从未见过她,对她盈生出了好奇。 然后我看见母亲流泪了,她的五指紧握住电话,和老妇人说了许多许多的话,可老妇人只是以单音回应着,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突然,母亲将我抱起,放在她腿上,于是我更看清了老妇人的面孔,她的面相很慈善柔和,对我笑的时候眼周上爬满了细纹,我觉得她是个好人,所以冲她露出了八颗牙齿。 母亲搂着我,说:“欢欢,她是外婆,快,叫声外婆。” 我先是一愣,然后字正腔圆地喊了声:“外——婆——”老妇人笑得流出了泪,对我赞许似的点点头,我继续说道,“外婆好,我叫祝欢,今年六岁了,明年我就要上一年级了!” 不一会儿,母亲又将我放了下来,继续对着电话和那头的外婆说话。没过多久,外婆便和那个男人走向了漆黑的小房间里。 那是我记忆中对外婆唯一的印象,从今往后的日子里,我再没有见过她。 可我始终认为我的外婆是一个好人,即使她因杀人入了监狱。 赵文梅是村里唯一的傻子。她没上过学,每天就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看着人来人往的村民们笑得乐呵。 村里人知道这女娃没有人管,对她多少有些同情。要说这孩子也真的可怜,父亲因为喝醉酒搞大了镇上黄花姑娘的肚子,没有脸面地抛下这对母女往外跑了;母亲陈兰花脾气不好,天天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骂天骂地,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男人跑了。 周围人知道陈兰花可怜,于是在富余下好心向她家送点儿吃食、衣料布子等。可陈兰花偏偏不爱受他人恩惠,心硬得很,以为邻居家的瞧不起自己,出口就似泼妇般地大骂。久而久之,村里人也不爱管陈兰花家的事情了。 要说赵文梅成傻子这事,还真要怪陈兰花了。 赵文梅六岁那年的一个傍晚,季节入秋,天气也渐渐转凉了,陈兰花依旧带着女儿去河里洗澡。赵文梅因此受了凉,夜里没有预兆得发起了高烧,辗转反侧浑身不舒服。 陈兰花睡在一旁眯着眼打呼噜,被赵文梅翻来覆去的声音吵醒了,烦躁地皱起眉头,伸手推了推赵文梅的后背,愠怒地低声道:“别瞎动,睡觉也不安分!” 等陈兰花发现赵文梅发烧之后,女儿已经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虽说陈兰花这人心硬脾气躁,但对赵文梅多少还是尽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在感受到身旁女儿浑身发烫以后,陈兰花一个激灵坐起身来,胡乱地摸着赵文梅的脸、脖子、手臂。 “赵文梅,臭丫头!赵文梅?”连着叫喊了几声发现没有应答,陈兰花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里油然营生起一股惶恐慌张。 当晚,陈兰花连外衣也来不及披上,跻拉着一双拖鞋,急忙抱着赵文梅去找村里医生帮忙。等孩子醒过来,一双空洞的大眼睛却痴痴地望着周围,呆滞得没有神情。 陈兰花当着众人的面,也顾不上尊严和面子了,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嘴里一边念叨着:“我这苦命的孩子噢,命生得这样不好......” 突如其来的发烧让赵文梅烧坏了脑子,自那以后,小女孩成了村里唯一的傻子。 日子依旧在哀怨与叹息声中度过。陈兰花依靠自己的手艺活勉强维持着两人的生活,她也不管赵文梅白天去哪儿鬼混,只坐在家中缝缝补补、等着赵文梅回来吃饭。 陈兰花了然自己的一生也就这样了,没有盼头的生活让她不接受任何人的好意和施舍,日子一眼望不到头,自然也不会去希望有什么特别。 直到,村里有了些许变化。 镇上领导说了,为了改善村里的条件,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妇女去厂子里工作,薪水不多但多少能补贴点家用。 陈兰花报名去了,领导体恤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很难过日子,于是顺利让她进了厂。 时代的潮流和变化让陈兰花发生了大改变,她不再和以前那般泼辣,对待身边人也开始和和气气,似乎以前那个性子火烈的女人一去而不复返。 陈兰花见到邻居会主动问好,说起话来也柔声细语。最初人们对于她这个变化很是诧异,而后才明白,陈兰花这是遇上了交好的男人。 那个男人叫高强,是厂里的中级员工,负责机器修理工作。人长得高大,面相又宽厚老实,因为前几次帮助陈兰花修好了机器,陈兰花很是感谢,这两人一来二往的,也酝酿起不可言说的气氛和情感。 周围邻居终于见到了这个让陈兰花改变的男人。那天,高强来到陈兰花家中做客,为了好好招待,陈兰花还特意去镇上花几块钱买了一只鸡。 高强来的那天,天正下着细蒙蒙的雨,乌云聚集,将湛蓝的天空抹上一层厚重的灰色。 高强看到门口有个小女孩,正蹲着,身体前倾看着地面上搬家的小蚂蚁。他走上前去,抚摸着女孩蓬松又凌乱的短发,问道:“小姑娘,下雨了,你怎么不进屋?” 赵文梅抬起头来,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直直地望着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她突然咧开嘴笑了,指着地上的蚂蚁,迷迷糊糊地说:“小虫子,小虫子......” “它叫蚂蚁。”高强怜爱地看着赵文梅,而后又问,“你今年几岁了?” 赵文梅傻兮兮地用树枝引着地上的蚂蚁,不理会一旁的高强。这时,陈兰花冒着雨回来了,她刚走进门,目光落在赵文梅身上,似嫌弃地瞪了一眼,说:“丫头,进屋,别感冒了!” 而后,眼神又溢出温情,对高强温声说道:“那鸡贩子少找了我钱,我回去要,又耽误了一些时间,你再等会,我这就去做饭。” 高强站起身来,指了指身旁的赵文梅,又问:“这是你孩子吧?挺可爱的,今年几岁了?” “十二岁。”陈兰花有些心虚,说话的声音略微低了些,生怕惹高强嫌弃。 高强神情一滞,面容流露出短暂的惊诧。他没有想到这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看着身子瘦瘦小小的,说话也不利索。 陈兰花不想说那么多关于孩子的事情,于是转身回到厨房去准备一会儿要吃的饭菜。这顿饭为了什么,两人心知肚明,她也知道自己有孩子这事是瞒不了的,索性也没让赵文梅藏着掖着。 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一旁的赵文梅咿咿呀呀地指着桌上的鸡。陈兰花静静地埋头吃饭,时不时给高强夹几个菜。 “兰花,咱俩以后的日子一起过吧。”高强看着碗里积成小山的饭菜,停下筷子,抬起头对陈兰花说。 听到这话,陈兰花先是一愣,而后情绪才化成泪水从眼眶中泛滥而出,她强忍住欲往桌上掉落的眼泪,哽咽着舀了一碗鸡汤到高强碗里,才说:“先吃饭,一会儿再说这个。” 村里人都说陈兰花的福气还在后头呢。高强实在能干,宽厚善良,其他未婚的女人都眼红,说陈兰花这是坏男人跑了,好男人赶上来了。 要说陈兰花也没有别的本事,除了一张脸蛋长得清秀白净,做事勤恳,若是她以前那个臭脾气,怕是全天下的男人见到她都得胆怵。 陈兰花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中,人也长胖了些。直到,几个月后,高强不见了,还带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她离异还带娃,却被优质男求婚,不久他卷钱消失才知被骗惨 等陈兰花发觉这其中不过是一场骗局之后,想后悔却已经来不及了。原以为女儿赵文梅不过是和平日一样,贪玩忘了回家。等天黑以后,陈兰花等了许久,等到过了往常的时间,也没见得赵文梅回家的身影。 女儿不见了,高强也不见了。当晚,陈兰花又变回了之前那个说话大声、脾气暴躁的女人,她也不在乎夜深人静,穿好外衣就往村居委家中奔走,一抡拳头重重地敲在村居委长的铁门上,卖力喊道:“村领导,我女儿不见了!”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知道陈兰花丢了个女儿,众人再联系高强也没有办法了,于是合理怀疑这是一场骗局。 出了这事以后,周围村民们都将房门关得严实,唠叨着自家孩子不要夜深了还在外逗留,平时和小伙伴们玩也不要去偏僻的地方,更不要跟着陌生人走。 陈兰花彻底绝望了,因多次去厂里寻要个说法,厂里怕影响,将她辞退了。自此,陈兰花大白天在厂门口和村居委会处两地轮流奔走,又哭又喊,嘴里重复着那句:“死骗子,你还我女儿......” 不久后,村里少了个傻子,多了个疯子。 林贵襦是光棍,直到三十岁,他终于娶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媳妇。 山村里的男人们羡慕得很,说是林贵襦出远门打工交了好运,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回来,每谈到林贵襦从外地娶回来的女人,他们便不由自主地用各种话去调侃林贵襦。 林贵襦媳妇哪哪都好,唯独脑子不太行,说话也不流畅,听说是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 “贵襦啊,脑子烧坏了也不碍着什么,聪明的女人难管,指不定哪天就给你戴顶绿帽子。” 不大不小的酒馆里,几个男人坐在狭窄的过道里喝着酒。 “是啊,要我说,这样的女人才好呢,听话。再说了,也不影响正事,大伙们,是不是?”说完,过道上传来一串笑声,循声而去,是一个身材高大,眼睛狭长的男人。 听到那个男人的调侃,众人仰头大笑,推搡着林贵襦说是捡到了宝。受气氛的感染,林贵襦心情大好,挥手大气地喊道:“今天这酒,我请哥们几个喝啦。” 欢呼声一片。夜晚渐渐落幕,月亮悄悄挂在枝头,林贵襦手里拎着半瓶酒,步伐摇摆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他面色红晕,哼着欢快俗气的小曲儿,慢悠悠地晃回了他的小砖房。 林贵襦回到家时,媳妇傻娃已经睡着了。 窗外月色皎洁,银白色的月光落在床榻上,铺洒在侧躺的傻娃身上,衬托出腰肢纤细,身材细瘦,即使穿着最为简单朴素的粗布烂衫,但这一切在醉熏的林贵襦眼里,撩拨动人。 空酒瓶从林贵襦的手里滚到了床榻下,他蛮横地朝傻娃扑去,惊得夜里乍然响起一声尖细的叫声。他粗鲁地撕扯着傻娃的衣服,满是酒气的嘴游离在她的脸蛋和脖颈,身下的女人拼了命地挣扎,可终究还是结束在一道清脆的巴掌声中。 窗外的乌鸦喑哑地叫着,月光渐渐黯淡失去了原有的光亮。 鸡在山头昂着头,扯着嗓子鸣叫。 傻娃捡起衣服,蜷缩在角落里,她很怕疼,即使这样类似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自从被妈妈的朋友带走以后,她感觉到身体在慢慢地变化,高叔叔告诉她,这是成为大人的象征。 在十四岁那年,傻娃第一次明白做大人的体验,她一点也不为此欣喜。 一直到傻娃十六岁,高叔叔带着她去见了林贵襦。初见他时,傻娃局促不安地站在高叔叔身后,一双水灵纯粹的双眼迷茫地望着眼前憨厚的打工仔,他穿着的确良衬衫,褶皱的裤腿挽起。 林贵襦笑起来时,傻娃怔怔地望着他,他和平常的高叔叔一样,面善老实。 “这姑娘长得真好,多大了?”林贵襦指着傻娃说道。 “上个月刚满十八。”高叔叔想要从身后将傻娃拽到面前来,可傻娃始终以茫然和警觉的眼神打量着林贵襦。 高强叹了口气,转身朝向傻娃,又勾起那个标准的笑容,“以后跟着这位叔叔好不好?他会带你吃好多好吃的。” 听到好吃的,傻娃的眼睛亮了起来。 “叫啥名?”林贵襦继续询问。 “没正名儿,我们都叫她傻娃。她小时候烧坏了脑袋,所以有些懵懵懂懂的,但不影响其他。” “这不行,得少些,人是傻的多亏啊。”林贵襦蹙起眉头,又望了傻娃一眼,和高强讨价还价。 “少不了,已经是最低的价钱了。”高强推辞,正想拉着傻娃转身离开,便听见林贵襦烦躁地啐了一口痰在地上,“行了行了,成交。” 于是,半个月前傻娃被林贵襦带到了这个落后的小山村里,在这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高叔叔,山里人和林贵襦的朋友时常叫她“贵襦他媳妇”。 傻娃看见林贵襦身边的男人对她贼兮兮地笑时,也不明白为何,她当是好意,于是扯着嘴角也回应他们傻气的一个笑容。 傻娃还是和以前一样,该做饭做饭,该扫地扫地,日子和以前在高叔叔家没有什么差别。 直到有一天,林贵襦的一个朋友找上了门,趁着林贵襦不在家,摸了傻娃的手,搂了傻娃的腰,还亲了傻娃的嘴。 傻娃感到不舒服,挣扎着想要从那个粗壮高大的男人怀里离开。可那个男人却不依不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你这臭娘们,昨天还对我笑得那么欢,不是勾引我是什么?” 等傻娃哭得晕了过去,再睁眼那男人已经离开了。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一切就和没有发生过一样。 两个月后,傻娃怀孕了。林贵襦欣喜地捧着傻娃的脸蛋,猛地亲了几口。 林贵襦一直期待着未来有一个男孩,于是他开始对傻娃很好,给她买好吃的好喝的,家务活也不催着她去干,做饭洗衣服都让她慢慢来,有时还会站在一旁帮她。 傻娃以为林贵襦在慢慢变好,在夜里不会再压着她喘息,不会喝酒以后就对她大哄大叫,甚至出手打她。偶尔的温柔让她想起了高叔叔,那个又讨厌又和蔼的男人。 肚子在慢慢地拢起来,傻娃以为自己生病了,压着肚子想要把它按回去。林贵襦见状,急匆匆地跑过来,半蹲在傻娃身边,握住她的手,轻声说道:“傻娃,你小心点,知道肚子为什么变大了吗?” 傻娃摇了摇头,呆滞地望着满脸堆笑的林贵襦。 “肚子里有了一个小生命,他在默默地成长着,你可不能把它杀死哦。”林贵襦抚摸着傻娃的腹部,而后又贴着肚皮,安静地倾听孩子的声音。 一听到“杀”这个字,傻娃惶恐地点头,喃喃道:“小生命,不杀死。小生命,不杀死......” 林贵襦笑得很开心,拍拍傻娃的后脑勺又离开了家。酒瘾上了头,林贵襦顾不了那么多,掏出口袋里的几枚硬币,吊儿郎当地朝着小酒馆走去。 “大壮,林贵襦娘们肚子里那孩子真是你的?” “那可不是!我之前和那娘们有过,啧,你们懂的。” 大壮醉醺醺地和身边人说着流氓话,时不时还得意洋洋地仰头大笑。林贵襦止步停在门口,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血脉喷张,拳头紧握,怒气一时涌上心头,他冲进屋内,拎起桌上的酒瓶,张狂地朝大壮的额头上砸去。 周围人吓了一跳,还来不及拦住,林贵襦手中的酒瓶已经砸向了大壮,只见大壮宽大的额旁流下了鲜红的血,正恼怒地瞪着他。 就在林贵襦想要再上前时,众人反应过来,连忙挟住他的两只胳膊,厉声制止。 “大壮,你他妈的!老子和你没完,敢动我媳妇儿,你等着!”林贵襦莽撞地冲上前,却手脚束缚使不上力,他手臂青筋暴起,连着说了一串的脏话,不堪入耳。 “老子上了怎么了!是你媳妇勾引我的!我去你妈的!”大头站起来骂道,忽感一阵晕眩,又坐在凳子上,架起一只腿,扶额忙招呼其他人过来搀他。 听到这话,林贵襦愣住,气不打一出来,转身离开了小酒馆。还没进屋,他拎起门口的扫把,在门外大喊:“臭娘们,老子不打死你!还有肚子里那个野种,亏得老子好吃好喝供着你们!” 当晚,林贵襦家传来凄厉的哭声和尖叫声,还有桌子凳子碗筷的落地声,又是沉闷,又是清响,住在隔壁的人家站在门口,唏嘘地望着屋内的狼藉一片,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多管闲事。 不一会儿,几个年长的男人冲了进去。渐渐地,女声息弱,片刻后,站在门口往里望的闲人们转移了视线。 一个男人背着浑身是血的女人,疾步朝外奔走。众人视线紧紧跟随,待那一行人消失在巷子口,才陆续离散。 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努嘴望向屋内,悠悠摇头说道:“造孽哦,造孽哦......” 傻娃肚子里的野种没有了,因受伤过于严重,以后再怀孕怕是难了。 经历了这桩荒唐事后,傻娃人消瘦了不少,头发散落在脸上,似人似鬼。林贵襦气愤地不再管她,任由她在山里游荡,听山里的孩子说,林贵襦家里有个傻女人,人傻,又笑又疯的,还常常喊着:“小生命,不杀死。小生命,不杀死......” 至于那个小生命是不是野种,也由不得他人去论证了。林贵襦远走了,离开大山——这个让他丢了面子和男人自尊的伤心地。 两年后,山里来了个大学生,气质温柔,穿着一袭白色衬衫裙,走在这片泥泞的山路里,与山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女大学生有个动听的名字,叫何花,听人说,这女大学生是让林贵襦拐骗来的,连书也没读完,就这样来到了山沟沟的地。 林贵襦在外面不知道找了什么路子,忽然发了一笔财,穿的用的都是现下的名牌,手腕上的表盘有鸡蛋那么大,表带上还镶着金,走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得亮人眼睛。 他挽着何花的肩膀,招摇地走在路上,时不时和周围人家打打招呼,唠唠话,大多是夸自己在外潇洒。一旁的何花不说话,默默地低着头,手指绞着裙子,看起来拘谨客气。 林贵襦回到家时,看着家里一切如常,他耸耸肩没有在意,径直走进灶房去给何花倒水。刚进房,傻娃正转过身来,满脸的灶灰熏得脸黝黑,林贵襦惊得往后退了半步,“见鬼!” 他没有想到傻娃竟然还会在家,于是走上前去,拍了拍傻娃的肩膀,说道:“去,倒杯干净的水。” 傻娃脸上闪过一丝害怕,身子忍不住地打颤,哆哆嗦嗦地退了几步后,又听到林贵襦那粗犷的嗓音:“听见没,倒水去!” 傻娃紧张地低下了头,手指蜷缩着给林贵襦倒了杯水,迅速地放在桌上后跑了出去。何花坐在大房间里,恰好看见的是一个纤瘦的女人从灶房里奔走出去。 林贵襦殷勤地给何花递上一杯水,谄媚说道:“我们山里条件不好,不过你放心,有我林贵襦在,就不会让你母子俩饿着。” 何花抿着唇,接过了水,想起刚才那个女人,她细声问道:“你屋内还有别的女人?” “噢?”林贵襦犹豫几秒,回答说:“你说刚刚那个傻娃啊,她是我远方妹子,脑子不好,你别介意。” 何花不说话了。待林贵襦出门以后,她耷拉着脑袋,垂眼看着自己还未凸显的腹部,仔细思量这一切做得是否正确,她不敢深思,因为她知道自己明明是错的,可到头来,还是没有勇气去反抗、去斗争。 一个女人的贞洁是这个世道上唯一干净的,容不得半点玷污,若是失去,则意味着你将被生活的唾沫星子淹没。这是小时候父亲告诉她的,可是为什么,明明不想承受且没有错误的那一方,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迎合世人们所谓的操守。 何花读过书,她深以为,一个女孩的品质不该由男人口中的贞洁来衡量。什么破鞋、公交车、荡妇,这些词语被有偏见的人强加在受过伤的女孩身上,凭借她们对恐惧的本能而放肆伤害。 然而,道理很少是用来践行的,而道德才是何花必须面对的,从小成长在谩骂的环境下、失去了父母的她,自卑脆弱,她经不起世人的指责和无声的指点,她不想走在大街上,接受他人带有攻击性的目光。 何花形容自己好似一朵风雨下的残花,即使想要坚强地生长,却还是得为暴风雨折腰。 认识林贵襦是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何花在饭店里当服务员,可这一天却成为了她永远无法和自己和解的噩梦。 何花在递菜时,不小心地将菜汤洒在了林贵襦的衣服上。从此之后,俩人有了交集,林贵襦花言巧语,何花害怕赔偿巨款,天真地被他骗回了家,等醒过来,才痛哭大骂。 林贵襦给了几百块钱当是对她的补偿,何花不稀罕,她本想举报,可一没证据,二是怕人唾骂。 何花因怀孕退学了,她没钱打掉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林贵襦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又找上了何花,对她柔声细语地说道:“小花,咱们结婚吧,你放心把孩子生下来好了,我们回家乡过日子,城里的业务我也不要了,咱们回去好好过日子。” 何花半信半疑地看着林贵襦,在心理防线多次挣扎和崩塌以后,她还是妥协了。 春去秋来,何花的肚子渐渐变大,林贵襦不常在家,偶尔晚上才会回来。两个女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个月,傻娃却始终含着仇恶的眼神望着何花。 何花能够察觉到傻娃眼里的敌意,当她尝试与傻娃沟通交流时,傻娃却怒吼一声,然后跑了出去。山里没有城里发达,何花带了几本书来,索性在纸上抄写打发日子。 经过林贵襦屋里的妇女们看见窗边有个书生气的女孩子在写字,都觉得是奇了怪的事。山里连考到初中文凭的孩子都屈指可数,她们见识短,又哪里见过大学生,还是女孩子读书的,那就更稀奇了。 何花很少出门,一来人生地不熟,二来林贵襦也多次告诫她不要在外面瞎走,容易受伤,山路崎岖泥泞,医疗条件又差,若是不小心摔了一跤那可是要命的。 何花不听劝,就想走过一条蜿蜒小路去山里的集市走走。林贵襦知道之后,竟头一次对何花发起了脾气,他面色青黑可怖,一时怒气没有忍住,出手重拍了何花的后背,当时她便惊得哭出了声。 自此,何花不敢随便走出家门,林贵襦吩咐了,若是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尽管让傻娃出去,她虽人傻,但做事方面还是机灵。 何花多次想要和傻娃说说话,都遭到了傻娃的厌恶,那是明晃晃写在脸上的情绪,她也不知道为何傻娃如此讨厌她。 直到听到村里人说闲话,何花才真真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不过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这个身份让何花气得差点站不稳。晚上,等林贵襦回来以后,何花手握菜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哭喊道:“林贵襦你不要脸!” 林贵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连忙说好话平复何花过激的情绪。一旁的傻娃站在小角落里,咧开嘴笑着,还稚气地拍起了手,林贵襦转过身去狠狠地剜了傻娃一眼,而后又慢慢向何花靠近,“你别生气!你先放下刀来,我和你好好说。” “我和这娘们早就离了,你别听村里人瞎说,我自从去城里走业务之后,就和她再也没有联系。回来后,我看到她在家也是吓了一跳,她脑子不好使,我看她可怜,也就没撵她走,就当是个干活的......” 见何花的手微微颤抖,林贵襦知她在心里思索,于是继续装作真情实感地说道:“你若是嫌弃她,我明天就赶她走!” 说完,迅速地朝角落走去,扯着傻娃的肩膀想要将她推出门去,傻娃不肯,扭扭捏捏地乱躲。这时,身后响起一道清脆的菜刀落地声,林贵襦忙转身,见何花只是蹲在地上放声大哭,他打心底松了一口气,趁着这个空子,傻娃又逃走了。 何花无奈,她知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打不了,只能被迫接受。她恨自己,为什么当初那么傻,又为什么要任由这个孩子在肚子里成长。 她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却也无法主宰和把握自己的人生,她自卑懦弱,胆怯又敏感,虽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脑子里的思想还是禁锢在以前的小农村里,她曾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她那该死的原生家庭,当父母亲去世以后,何花却又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真的没有了指望。 何花不再和以前一样,对林贵襦抱有期待了。或许这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她不过是一只落在网里的小鱼,在自己建构的理想鱼塘里没有见过真正的鱼钩,所以才会在被捕上岸以后,天真地幻想自己曾是因诱惑的鱼饵上钩。 从当初到现在,没有诱惑的鱼饵,只有受世俗束缚和不敢游回水里的小鱼。 何花心如死灰,在看透本质以后,她每天数着日子过,终于还是等到了分娩的那天。 若是没了傻娃,何花不知道该如何平安地生下这个孩子。 剧痛袭来的那个傍晚,何花依旧坐在窗前翻动着书,那些书已经有了变旧腐烂的痕迹,感觉到腹部疼痛是没有征兆的,何花咬牙想要站起身来,痛觉让她又坐了下去。 书落在了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何花伏在桌上,两腿之间有液体在流动,她仰起头扯着嗓子想要喊人。 正在这时,傻娃回来了,她手里捧着一束自摘的野花,满脸傻笑地走进屋,突然看到何花苍白如纸的面容,张着嘴似要喊什么话。傻娃走上前去,才看到她的粗布裤子上有了一些血迹。 傻娃怕血,她面色惊恐地跑了出去,何花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此时却只能期望林贵襦能快点回来。 半分钟左右,傻娃跟着邻居几个妇人走了进来,嘴里支支吾吾地说不清话,依稀听到“小生命,别杀死”的字音。 一行人焦急地将何花送到了邻近接生过的婆婆家中,几小时后,何花肚子里的孩子才顺利落地。 一声啼哭嘹亮,何花虚弱得昏睡过去,站在角落的傻娃看见带着血的布条,转过身去嘀咕着“别杀死,别杀死......” 林贵襦回来之后,得知何花已经生了,身体颤抖地站在门外询问道:“男娃女娃?” “是个女娃娃!”里屋一个妇女朝门外大声回应。 林贵襦心头的一腔热焰被浇灭,近十个月的期待化作了死灰。他沉默地低下头,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自顾自地走到屋后,坐在废弃堆里抽着,心中却怎么也不甘心。 何花醒来以后,看着自己的孩子,鲜少露出了微笑。傻娃站在床边,伸长脖子望着襁褓中的小娃娃,撇着嘴说:“这是小生命。” 何花第一次听见傻娃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微微抬头看向傻娃,对她微笑,有气无力地说道:“谢谢你,傻娃。” 傻娃听到这话,脸不知怎么红了起来,又转身要逃。自何花生下孩子之后,两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无形中消逝,傻娃会主动将碗筷放在何花面前,洗衣服时也不再将她的衣服拎到一边,连何花常常看的书,傻娃也整整齐齐地堆好。 何花以笑回应,两个人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孩子满月那天,许久没有回家的林贵襦回来了,满身酒气,身上体贴的西装也皱得不成样子,他一进门,眼神冷淡地扫视了一眼屋内,看见正在喂女娃喝母乳的何花,他心中突升的烦躁,走上前去,用力推开何花的肩膀。 女娃一时没有喝到母乳,张着嘴望着何花,不一会儿就嚎啕大哭起来。何花不耐烦地瞪了林贵襦一眼,语气稍有些厌倦,“没见着孩子正饿着吗?” 林贵襦处于醉晕的状态,脾气本来就不好,见何花似有反抗他的势头,没有控制地往她脸上呼去,“死娘们,不许这样和我说话,活腻了吗?你生的是女孩,养那么好干什么?长大以后去勾引男人啊?” 如果说没有预兆来的一巴掌和前面几句话尚且还能让何花强忍住的话,那么后面关于女娃的一段肮脏的、没有半点依据的疯言疯语,才真得让何花怒不可遏,她仰起头狠狠地瞪了林贵襦一眼,没有说话。 此时的沉默不语和满含仇恨的眼神已经胜过了一切怒骂。何花明白,和他这样的人是讲不通道理的,喝了酒之后平白无故地发起疯来比清醒时更不可理喻。 “你他妈敢瞪老子?”林贵襦正想再扇何花一巴掌时,傻娃突然站在门口大喊起来,冲向前去环住林贵襦的腰,咬牙切齿地抱住他往后退。 林贵襦气得脸涨红,他使劲力气想要掰开傻娃粗糙的双手,可傻娃却抱得很紧,她咿咿呀呀地叫骂着,听不清话里的内容。 林贵襦累了,因酒精上头,他瘫坐在地上,作罢不再去挣扎。很快,他换了一张嘴脸,无奈地指了指灶房,对傻娃说道:“去,给我煮个面,我饿了。” 傻娃松开了手,瞥了一眼坐在床上不知所措的何花,见林贵襦的脸孔不再那么吓人,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向灶房去给林贵襦煮面,偶尔走回来一看,林贵襦已经睡倒在地上,打着巨响的呼噜声。 何花产后抑郁了,她奶水不够,山里条件又差,孩子没有补充到营养,一张小脸瘦得和猴子面似的。 她来到这之后,唯一的念想就是这个女孩了,一想到前几天孩子感冒没得医治,连夜得哭泣,何花很不好受。 傻娃也想了好些办法逗孩子开心,比如从山里野花丛中摘了好多花,编成花环给女娃玩。可那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懂这些,何花摇了摇头,眼神忧郁地望着傻娃。 何花实在没有一点奶水了,眼看着孩子饿得发慌,她没有办法,急得哭了起来。家里没有钱,林贵襦又很久没有再回来,真不知道将来孩子该怎么成长起来。 傻娃站在一旁发愣地看着女娃发黄的脸蛋,想到什么,她眼睛发亮起来,拍了拍何花的肩膀,然后指向了自己,她期待地等着何花回应。 何花思索了片刻,才明白傻娃的意思,她感激地望着傻娃,眼里蕴含着泪水,几天几夜的煎熬和难以入眠,已经让这个母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她崩溃地掩面哭泣起来,而后拉起傻娃的手,连声说了好几句谢谢。 傻娃任由何花握着她的手哭泣,大人的哭泣是细弱低声的,哭声里蕴含着对生活艰难的辛酸和人情世故的煎熬。 一旁小孩大声哭喊着,她为饥饿呐喊,是因未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向世界宣叫。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只是将我当成发泄的道具,不仅撒干了欲望,而且还卷走了我的钱。 没过多久,何花默默擦拭着眼旁的泪水,将床上的小孩抱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傻娃的怀里。两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过着紧凑却朴实自在的生活,林贵襦不在家的日子,何花洗衣服带孩子学着做针线活,傻娃做好饭等着她们俩一起吃,还想尽办法要给孩子吃最好的、逗孩子开心,见到小娃娃,傻娃总是笑得很开心。 有了两个女人的悉心照料,娃娃越长越可爱,面色渐渐红润,也不似以前那般干瘪。等到孩子学会开口说话时,模糊却可爱的一声“妈妈”差点让何花落泪。 她们平静没有波澜的一天天伴随着娃娃的成长,变得飞快起来。何花没有想到,在安安八岁那年,林贵襦会突然回来。 他穿着一声破旧的西装,上面拂着细细的一层灰。瘪皱的公文包硬生生地夹在咯吱窝下,胡子邋遢地挂在下颌线,眼神黯淡无光,面相却更尖酸刻薄,一副流浪汉的模样吓得何花手中的针线盒落地。 林贵襦似乎根本没有许久未归的感觉,他迈着步伐走向床边,连鞋也不脱,习惯地将公文包扔在一旁,自然地往后仰,躺在床上架着二郎腿悠悠地摇摆起来。所有动作习惯自然,仿佛昨天才下班回到家。 这时,傻娃和安安一起回来了。在看到林贵襦的那一瞬间傻娃的笑容消失了,她转身拿起门外的扫帚,疾快地朝林贵襦奔去。 一个扫帚打在身上,林贵襦张眼就看见怒目圆瞪的傻娃站在床边,他惊得从床上起身,顺口就爆了一句粗话。 傻娃只是瞪着眼睛看着林贵襦,她没有说话。一旁的何花将安安搂在怀里,轻拍着她的后背。 林贵襦懒得搭理傻娃了,径直从她身旁穿过,走到何花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和怀里的女孩,声音没有一丝感情,问道:“长这么大了?” 何花听林贵襦这么一问,生怕他打孩子什么主意,于是紧紧地抱着安安,不回答林贵襦。 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林贵襦见状,冷笑地推了一把何花,“哑巴了?老子问你话你不回答,是不是看不起老子?” 林贵襦转过身去,不爽地瞥了傻娃一眼,慢悠悠地走到她面前,从她的手里将那把扫帚夺走,下一秒就往傻娃腿上抽,怒狠狠地大吼道:“敢打老子?这么久不回来真当老子死了是吧!” 傻娃忍着痛没有叫出声,何花在一旁却倒吸了一口气。她快要哭了,见傻娃依旧冷眼看着林贵襦,她摇了摇头,示意傻娃不要莽撞。 林贵襦的目光来回在两个女人之间,他突然扔下扫帚,姿态散漫地坐下来,指着她们俩说:“你们俩安分点,我现在回来了,你们就得好好服侍照顾我。” 何花低着头,安安刚才听到陌生男人的吼叫声,此时害怕地哭了起来。林贵襦听见,不耐烦地眉头紧皱,“哭什么?老子还没死!” 安安的哭声更大了,何花在她的耳边轻咛着:“安安乖,安安不哭。”一手从上往下捋平她的恐惧情绪。 傻娃不理林贵襦,走到何花面前,下巴往门口一抬,说一个字,“走。” 林贵襦看着她们仨的背影,不屑地轻哼一声,“在老子地盘还不听话,女人就是他妈的烦人。” 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一个女孩。男人好吃懒做,酗酒凶猛,不务正业,自突然从城里回来以后,变得更加蛮横无理,抓着一点儿小事就骂骂咧咧,天天嫌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玩。 转眼安安十二岁了,她从小就懂事,主动帮大妈妈穿针线,还有小妈妈,对她总是很好,虽然每次问她话时回答得都不准确,可安安还是很喜欢小妈妈,因为小妈妈总会给她做好吃的,还陪她一起去玩、摘野花、逛集市。 不管是何花还是傻娃,安安都亲得很。唯独对家里那个男人,她是不乐意与他说话的,甚至不想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尽管他多次命令说,要叫他爸爸,可在安安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爸爸。 这个男人一喝酒就喜欢骂人,喝凶了甚至还会对两个妈妈动手,安安从小就被保护得很好,只能眼睁睁地站在角落里看着妈妈被打,却不敢反抗。 偶尔有一次,傻娃妈妈愤怒地朝男人扑去,本想抡起拳头打他,可没有想到力气根本不够。 林贵襦知道傻娃对何花好,于是每次都拿何花威胁傻娃,傻娃人傻又善良,于是再也不敢和林贵襦抗争了,因为只要她反抗,那个男人就会拎起棍子去打何花。 慢慢地,安安知道,大妈妈身上伤痕最多,总是一个人在夜里默默哭泣。傻娃妈妈怕她被男人打得更多更恨,每次只能冲在大妈妈身旁,抱着她,一边哀嚎着,不知在大叫什么。 那个男人伤害了安安最亲近的两个人,所以她非常讨厌他,甚至希望他永远消失在这个家里。 后来,这个男人真的再也没有出现过。 林贵襦之前欠的那一笔债终究还是追到了了他头上,他本来就做的不是什么大买卖,说的难听点不过是些坑蒙拐骗的玩意儿。 几年前,有人吃他卖的减肥药丢了命,拉他入伙的那个大老板早就一屁股走人,还将公司所有的业务转到了他手下,林贵襦因此欠下了巨额债款和赔款。 他不可能还上这一笔债的,于是趁机逃了出来,回到这个僻远的小山村里一躲就是三年。就在林贵襦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翻篇了以后,债主出现了。 当晚,林贵襦从酒馆里回家,连夜把柜子里的钱翻出来,动作慌张,想要着急地离开家。可仔细一想,那些债主既然能寻到这里,再往外逃怕是落网更快。 他的动作缓了下来。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他猛地回头看向那边站在角落的安安,目光变得神秘诡异。 何花站在一旁看着林贵襦焦急慌张的样子,多少有些疑惑,可当他的眼神落在安安身上时,何花心里一紧,搂着安安肩膀的力度又大了几分。 林贵襦没有时间了,他喝醉了酒,脸上晕出一抹邪恶的红,双眼发光,勾唇奸笑,像一匹饿狼朝安安扑去,一把推倒何花,将她怀里的安安拽了过来。 “你干什么!”何花冲着林贵襦大吼。她一向不对林贵襦大声说话,可孩子是底线,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活下来的念想。她朝林贵襦奔去,再次被他推倒在地后,死死地抱住他的小腿。 “死女人!滚开!”林贵襦用力踹开何花,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她消耗,于是目光所及一把耕田的耙子,因酒精上头,平时打惯了手脚又没个轻重之分,他作势要挥起它,向何花舞去。 何花的头当即流下血迹,感觉到罪恶的眩晕感,她抱着林贵襦的力度弱了不少。林贵襦看到血后并没有及时反应过来,反而还很得意地笑了:“死女人就是麻烦事多,再敢动老子,老子要你的命!” 骂完,林贵襦还没尽兴,看着脚边脆弱不堪一击的女人,他又不耐烦地往她的腹部、背部狠狠地踹了几脚。 林贵襦的手臂勾住安安的脖子,力度不自觉地加大,只见安安的小脸渐渐红透,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哭声,她看见妈妈的额头上流了好多的血,以为妈妈被这个坏男人打死了。 安安扑腾着自己对手和腿,想要从坏人的手臂中挣脱束缚,可谁知林贵襦感觉到小东西在挣扎,手臂箍得更紧。 何花的意识渐渐模糊,她仿佛看见,在林贵襦呲牙咧嘴的阴险笑容背后,有一束明亮刺眼的光朝自己对瞳孔穿射过来,它挑战着一个母亲的极限,让何花无意间摸到刀柄的那一刻,抛弃了所有的思绪。 仅这一次,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是时候勇敢地反抗了。 林贵襦的胸膛插着一把刀,滚热的鲜血溅在一张坚决狠毅的面孔上,模糊了视线。随即,难以置信的瞳孔放大和轰然倒地的沉闷声,成了这场悲剧的落幕。 傻娃目睹了何花毅然决然的过程,她差点惊恐地叫出声,原怕见到血的她不顾一切,狂奔到何花面前,用粗糙的手肆意地擦去何花脸上的脏血。 傻娃的手掌心因血红渐渐染上刺目的红,她的双手在颤栗着,望着何花,眼泪却止不住地往外流,她的哭是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年来,傻娃从来没有哭过。 傻娃说话没有逻辑,也不清晰,何花第一次见傻娃流泪,却笑了起来,低头看着傻娃的两只手,满是血红,她终究还是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一个拼命想要说些什么话,另一个却沉默地微笑着。安安紧紧地抱住妈妈,将头埋进她的怀里。 这一夜,沉默代替了所有罪恶的果实。何花明白,这是她人生仅有一次的勇敢和反抗。 "赵文梅,女,32岁,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这是当时媒体报道,关于我入狱外婆的新闻。报道中说了她很多坏话,有说她年轻出轨不守妇道;有说她装疯卖傻骗人钱财;还有说她虐待孩子杀害自己男人。总而言之,全是负面评价。 我曾问过母亲,是否真和新闻报道里所说的那样,外婆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坏女人。 母亲只是摇了摇头,捧着外婆的遗像痴痴地望向窗外,眼里似乎含着晶莹的泪珠,她什么都没有给我解释,只简单地我说:"欢欢,你要相信,你的外婆是个好人。" 我点了点头,凭借着对外婆的第一印象,我也认为外婆根本不想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坏。 在我家中供台上,有两个女人的黑白像,一个眉目清秀,目光柔和,白色衬裙上搭着两根小辫,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妈妈说,在我还没出生前,这个外婆就生病去世了。 另外一个便是我见过的外婆了,她的遗像并不好看,粗糙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眼神略显呆滞,挽起笑容却有些傻傻的样子,但我细细地看,总觉得慈眉善目,亲切得很。 母亲拉着我的小手朝这两位外婆焚香拜了拜,她每次都会流泪,我猜母亲一定是想她的妈妈了,于是我抱了抱母亲,仰着头对她说:"妈妈,你不要难过,你有两个妈妈,她们一定和你爱我一样爱着你。" 母亲听了这话后,哭得更厉害了,她拍了拍我的脑袋没有说话。 往窗外望去,两只白鸽在碧蓝的空中扑朔着翅膀,停留在窗台上热闹地低鸣着,母亲见它,手掌捧着小米粒递了过去,望着它们欢快地飞走,母亲目光深远,轻声说了一句。 “下辈子,你们也要成为自由自在的白鸽。” 不受坏人欺骗,不受家庭伤害,不受他人诋毁,不受世俗牵绊,骄傲地飞向远方。 我很庆幸生在一个自由的家庭里,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特别是我的母亲,要为自己的一生负责也要为自己的一生做主,所以即便是我日后在婚姻上的选择也是讲究喜欢且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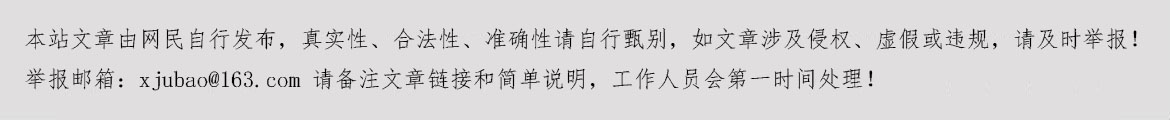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 新闻资讯
• 活动频道
更多




